秀兒(01-11)
破敗、凌亂的空間裏,眼前略顯臃腫卻掩飾不住華貴氣息的男人顯得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但是,他的臉上並沒有因為涉足這塊骯髒的地方而帶來的絲毫不耐與不滿,相反的,他的笑很謙卑,甚至有點諂媚。
這樣的人不好應付,擁有足夠高的地位卻能放下身段的人都不好應付,我討厭這樣的人,卻也因為這樣一個男人在我面前露出諂媚的表情而暗暗地沾沾自喜。
因為我是瘸子王,我的身份迫使他必須這樣做。
瘸子王並不是什麼體面的身份,卻是掌管着這座城市地下世界一部分的王者。
我掌管的人,不是紅燈區聚集的流鶯,不是人羣中竄動的毛賊,而是那些每個人出門都會遇到的,或是嫌棄,或是同情,或是視而不見的乞討者。
有人戲稱我們為丐幫,把我叫做幫主,但我知道我、我們和那些書中總是與俠義伴隨的叫花子們並不一樣。
我們不是體面的人,也不做體面的事。
面前的男人姓周,與我總是隱身在黑暗中不同,他是永遠暴露在陽光下,閃着刺眼光芒的那位。在外面,所有人尊稱他一聲周局長,因為他是這座城市白道的王者。
但是,在這裏,我們叫他周老闆,就像他叫我王老闆一樣,這是生意人之間的稱唿。
是的,生意。黑與白,光與影,自古以來不曾分開,相互對立也相互依存。
在數百年的繪本閒話裏,充斥着雙方明爭暗鬥到魚死網破的故事,但也不乏兩面勾結,共同做些見不得光的事情的例子。
很顯然,面前這一位,選擇了後者。
周老闆今天帶來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符,不是什麼隱喻,就只是一個製作粗糙,個頭也不大的裝在粗布香囊中的護身符。這種東西,可以在很多廉價地攤上買到。
但是,常人能買到的只有它的表皮,絕對買不到裏面那些看似普通卻價愈黃金的白色粉末。
而我們今天要談的生意,就是從此以後我手下的叫花子們開始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暗地裏為他兜售這些粉末,回報,是足以令大多人為之側目的金錢。
瘸子王不缺錢,手下的兄弟也不缺。不體面的人,多得是來錢的方法。但是,讓白道的王者親自送來的錢,我們平日賺不到。
斷手的眼睛裏已經流露出貪婪的目光,但我知道那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一種説不清道不明的感覺,一種可以在暗地裏,和昔日對立的那些傢伙們一起操縱着這座城市一部分的興奮感。
斷手是我最好的兄弟,也是我最好的保鏢。一個不體面的人卻帶着保鏢是很可笑的事,但是從我自己的經驗我知道你永遠不會想到這世上誰會忽然跳出來給你一刀。我也知道,無論是誰要對我不利,斷手的刀子,一定會比那個人的快。
斷手原本是個賭徒,仗着早年學成的一手刀法在賭場上橫行無忌。只是他刀法雖好,賭技卻着實差了些,積債過多,性子又莽撞,終於惹了不該惹的人,砍掉了他那隻玩刀的右手。
好在沒有人知道他的左手其實和右手一樣快,除了我。
斷手的債是我還的,被我救下時,他已一無所有,於是接受了我的邀請,成了我的左膀右臂,保護着我,讓我能在此刻威風凜凜地坐在特製的輪椅上,居高臨下地面對着那個白道的王者。
也正因為如此,看到他眼中的興奮與貪婪,我不得不多做考慮。
一個人能走到什麼位子,説起來也許是這個人能力的體現,但更多的時候,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一個又一個的巧合把我們推到如今的地步罷了。十幾年前,我沒有想過我可以坐在這裏,但既然現在在這個位子,就不得不用這個身份來處理事情。
有些東西我不想碰,這和我是否體面無關。但是,瘸子可以是一個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人,瘸子王不行。
「痛快!」
交易達成,周老闆起身拍掌,面上喜笑顏開。我雖然不如他般喜悦,但一眾兄弟都在起鬨,也只好陪着笑。
在這塊地方,歷代掌權者無論行事風格如何,所涉及的東西從不離乞討二字,今日瘸子王卻將兄弟們帶上別的路,正確與否,我不得而知。
「今天來談生意,其實還給王老闆帶了份禮物。怕王老闆説我不地道,所以直到此刻一切談妥才敢提出來,不過好禮不怕晚,想必這份大禮王老闆一定會滿意。各位請稍候一下。」
我以為已是結束,卻沒想到這人還準備了餘興,看他説得自信,心裏也有點期待。他轉身而出,片刻後帶了個女人進來。
我不知道看到這女人的一瞬間我是否掩飾住了臉上爆發的震驚,但也許在一眾兄弟們的吸氣和吞口水聲中,也沒有人會去在意我是什麼表情。
那是個很美麗的女人,美得驚心動魄,美得令任何見過她的男人都無法忘懷,遠勝過平日裏在外面見到那些已足夠讓人垂涎三尺的庸脂俗粉,也遠勝過十三年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她的樣子。
秀兒……
我驚叫,卻無聲。
「怎麼樣?小鳳仙可是我手下的頭牌,王老闆還滿意吧?」
周老闆看到了在場所有人的反應,也看到我呆愣的樣子,面色自得。而我聽到的,只有小鳳仙、頭牌,這兩個詞。
誰都知道,它們代表什麼。
「小鳳仙這名字,雖然是出自一個妓女。但這妓女是赫赫有名的只配英雄的妓女,所以這名字也不是隨便哪個妓女配得上的。」周老闆在白裙及地,長發飄飄的秀兒臉上輕佻地撫摸了一下,「這個女人,絕對配得上這個名字,也絕對配得上王老闆這樣的英雄人物!去,跟王老闆打個招唿!」
我知道他最後一句話並不是説給秀兒聽的。
十三年未見的女子,如仙女般款款行走至我面前,右手在腰側輕拍一下,葱葱食指指向我後,大拇指向上抬起。
「王老闆,小鳳仙跟您打招唿呢!」周老闆大笑了一下,走到秀兒身邊,摸了摸她的頭髮,「這丫頭,人雖然漂亮,又聰明,但是不會説話,也聽不見,也沒讓她學唇語,所以不管什麼時候都能叫來伺候,根本不用擔心提防,你不知道她有多受歡迎!」
我知道的,即使當年她不是現在這傾國傾城的樣子,也仍是很讓人喜歡的女孩。
而且,我也看得懂她的話。
瘸子王並非天生就是瘸子王,但我確實天生就是個瘸子。二十七年前被扔在孤兒院門口的一個雙腿萎縮的畸形嬰兒。
六歲的時候,一個男人來院裏帶走了一大羣孩子,都是有殘疾的,當然也包括我。他姓常,是我的養父,也是上一任的「老闆」。
孤兒院條件簡陋,所以走的時候除了一張破舊的必須要有人推才能動的輪椅,我什麼也沒帶走。而那台輪椅,也是這輩子陪在我身邊最久的東西。
那時我們都要把常老闆叫老爹,我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大清早被人推到鬧市區,扔在地上,到了晚上再被接回來。
我那時的名字就是瘸子,這個稱唿算抬舉我。因為瘸子還勉強能走路,但我殘廢殘得徹底,趴在街上很是引人注目,所以收入一直不錯,也一直討老爹喜歡。
直到認識秀兒。
秀兒是我十歲那年被老爹帶回來的,和我一般年齡,雖然不會説話也不會聽,但一雙眼睛水靈靈地放着光,模樣很是討人喜歡。至少,我第一眼看到她就知道我喜歡上了這女孩。
如今,這雙大眼依舊水靈,並且在目不轉睛地看着我,但我猜測她已認不出我。畢竟當年的瘸子還是個孩子,但現在的瘸子王已是個一臉兇相,疤痕遍佈的男人。
「愣着幹什麼?打招唿是這樣打的嗎?」
周老闆的話秀兒聽不到,但是他們有更直接的溝通方式。那隻毛茸茸的大手離開秀兒的長髮,在她的屁股上重重拍了一下,秀兒便立刻意會,向前一步在我面前跪了下來。
我不知道要調教多久才能讓一個聾啞人對肢體命令如此心有靈犀,但我知道秀兒對周老闆順從的樣子讓我無比心酸,還有,憤怒。
我揮開了秀兒伸向我襠部的小手,然後周老闆的臉立刻沉了下來。
「這禮物王老闆不滿意?」
「滿意,當然滿意。」即使看似平起平坐的場面,我也不認為自己真的有能力去招惹他,「只是,這裏人多了些。」
「哈哈哈哈!」周老闆像是聽到了個好笑的笑話,「我聽説瘸子王仗義,尤其是玩女人,有自己的肉就有兄弟們的湯,所以從不避諱。今天怎麼説起人多的話了?」
他頓了一下,目光瞥向秀兒:「我明白了,是我們小鳳仙看着可憐,王老闆起了憐香惜玉的心了吧?嘿嘿……告訴你,這丫頭雖然長得跟個仙女似的,但是骨子裏,比妓女還賤……」
下等人最愛欺負下等人,藉此來讓自己覺得能高人一等,但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這道理我懂,卻沉迷其中。
不體面的人做不體面的事,這和我、我們有沒有錢沒關係。用真實的身份去壓迫別人才會覺得刺激,才有興奮感。所以在這間舊倉庫裏,瘸子王沒少招來市裏有名的紅牌妓女,玩些為人不齒的眾人共淫的勾當。
那些婊子當然不會願意,但走進了這扇門,命就不是她們自己的。昔日的瘸子,到今日的瘸子王,雖然聽起來只差了一個字,這一個字卻包含了太多的聲名狼藉,我是城中一霸,沒幾個人敢惹。那些妓女不敢,她們背後的人也不敢。
但是沒幾個人不代表沒有人,我們也曾踩到過不該踩的點子,那些點子,都籠罩在一個周局長的名字下面。
所以,我和周老闆雖素未謀面,卻早有梁子。今日,他不會一直讓我在他面前高高在上下去。
當眾搞妓女,對我來説不是什麼為難的事。兩條腿比別人少了一截,縱使聲名顯赫,終究廢人一個。真要動起手,我怕連一個女人也鬥不過。但是威風凜凜的瘸子王不能告訴弟兄們我搞不定一個妓女,所以從第一次玩女人,我就把自己置身於弟兄們的目光下。
借人多之威,掩自己之弱。
他們以為我喜好這口,又有好戲可看,從不曾提出異議,久而久之即成習慣。
所以今天場子裏這塊肉,在他們眼裏就和以往任何一個妓女一樣,是有他們一份的。
只是,這個妓女曾經叫秀兒。
秀兒再次把手伸向我褲襠的時候,周老闆一言不發地盯着我的臉,我沒有阻止,連點異樣的表情也沒敢做出。
任何人一輩子都可能勇敢一次,一次勇敢便可能改變一生。但是,並不代表這一次勇敢之後他就不再是一個慫人。
秀兒解開了我的褲子,下身的衣物對我來説只做遮羞之用,一層單褲外就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她也許沒想到這麼快就直接見到我的陽物,略驚了一下。
我罕見地有點赧然。在這倉庫裏我算是個大人物,但是大人物並不一定什麼都大,斷手曾跟我玩笑説我幹過的女人下面絕對不會松,我自然也不會在意這個。
男人射精時候的感覺都差不多,雞巴大不大,那是應該女人關心的事情。
可是面對秀兒的時候,我很希望她從我褲襠裏掏出來的是一根大傢伙,而不是一條很久沒洗,散發着臭氣的短小東西。
周老闆看我不再拂他面子,掃了我胯下一眼便轉身落座,冷眼旁觀。秀兒褪了我的褲子,在雞巴上擼了兩下,垂首張嘴把它含了進去。
不是沒見過她與男人歡好的樣子,但第一次見到她吞吐男人的陽物,而且這陽物的主人是我。即使再多的偽裝,在此刻的舒爽之下我也不禁露了底,悶哼了一聲。
斷手吞了口口水,訕笑着向前走了一步,我心裏一緊。
瘸子王的女人,只有斷手可以一起淫玩,玩過之後再丟給其他兄弟,數年來一直如此。我想攔他,卻不知作何開口。秀兒嘴裏緊了一下,我一窒,斷手那隻僅剩的左手便搭在了秀兒的肩上。
秀兒穿的白色長裙,跪下來裙擺便鋪了一地,領口微垂,春光乍泄,我的角度看得清楚,斷手看不到,卻做得更直接,左手順着肩膀撫着便進了秀兒的衣領。
我看到薄薄的布料上鼓起一個手背的輪廓,不作停留地一路向下,覆蓋上了秀兒胸前的豐盈,之後便變換起形狀,揉捏擠壓。秀兒胸前受襲,卻不動神色,只把注意力放在我的雞巴上,一如之前不受我的惡臭影響一樣。
我心裏一半是火,一半是冰。火是秀兒挑起來的,因為她那張小口伺候男人的技巧勝過我以往經歷過的任何女人,素手香唇吹舔撫攏幾下,便帶給我前所未有的爽利感;冰也是秀兒凍下的,因為昔日我眼裏冰清玉潔的女子,此刻卻對連妓女也不願做的事情慣如穿衣用飯,全無一絲不願。
老爹帶回秀兒時,我也剛剛乞討回來。他把秀兒帶到我面前,指了指我,又對着她用手比劃了一堆東西。我看不懂,只看到秀兒點了點頭。
「你,以後對她多照顧點,多教點!」
他如是對我説,我像她一樣點頭。
之後我們便走得很近,當然只限於晚上回到倉庫以後。白天裏我們各有各的地盤,互不幹涉。
秀兒聽不見我説的話,我也看不懂她打的手語,彼此間倒是互相看着的時間多一些。我不知她的感覺,但我很滿足這樣,不,説是滿足,但其實怎樣也看不夠。足足兩年時光也看不夠。
秀兒雖伶俐可愛,但在外面的人看起來也不過是個蓬頭垢面的小丫頭。裝聾作啞最容易,所以不是每個人都相信這是個殘女。她能給老爹賺到的,並不多。
兩年時光,在我這殘廢的瘸子身上看不出什麼光影,但足以使秀兒逐漸出落的亭亭玉立,開始由小丫頭向一名少女蜕變。她越來越吸引我。
我開始想和她説點什麼。不是平日裏笨手笨腳的用肢體比劃,而是用她聽得懂的話,跟她説點什麼。
只是,無法出口,一如現在。
秀兒將我的雞巴含得很深,吸得很緊,斷手也將她的胸脯揉得很重,捏得很狠。周老闆好整以暇,臉上笑得高深莫測,眾兄弟則是毫不掩飾滿臉色相,吞着口水等着分一杯羹的時候。
我知道我無法堅持多久,秀兒的手指、唇舌靈活得超乎想像,片刻時光就使我忍不住想要不堪地交出精液,而斷手也不再滿足於這隔靴搔癢的觸弄,將手抽了出來。
斷手只剩一隻左手,自然無法像其他男人那樣將秀兒的衣服一把撕開,但是他有一把隨身不離的匕首,無事便拿出來把玩磨礪一番,吹毛斷髮,鋒利無匹,最適合割開女人的衣服。
見到斷手的手中刀鋒,兄弟們知道到了好戲上演的時候,大聲起鬨起來。周老闆依舊不動聲色,秀兒依舊吞吐不停,我依舊猶豫不決。
緞子般的黑色長髮被撥開一邊,秀兒衣背上有一條拉鏈,從後頸直到背中,但斷手視而不見,刀刃從秀兒潔白的頸側處探入衣襟,反手轉向,挑起那層薄紗料子。
刀鋒不斷向上提,收攏了秀兒身前的春光,露出她勒着一條細細胸罩帶子的裸背。我目不轉睛地盯着,不知所措,卻暗帶期盼。
薄紗終于禁不住刀刃的鋒利,一聲輕響後破裂開來,裂縫從上至下蔓延,隨着衣料的松垮垂落一直延伸到後腰上,無袖的白裙上半截便就這麼掛住秀兒的雙肩,將一大片雪白的嵴背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
嘬……嘬……嘬……
秀兒若無其事,將我的雞巴吃的嘖嘖有聲。
嘶……嘶……
斷手刀刃不停,又挑斷了秀兒肩上的布料。整個上半身的衣物終於無力地垂脱,讓秀兒巧奪天工般雪白的上半身呈現出來,除了一件胸罩外再無遮掩。
「嚯!嚯!嚯!嚯……」
弟兄們看到斷手的刀刃緩緩向那條細帶移動,自發卻整齊地哄叫着毫無意義的助威聲,斷手嘿然一笑,刀鋒已鑽進細帶和裸背中間。
我的目光,全集中在秀兒那內衣遮不住,露出一半有餘的豐盈雪乳之上,心跳急促的厲害,雞巴也脹得幾乎裂開,忍不住想要伸出手去將它們細細把玩一番。
但是,起鬨聲將我喚醒。
我知道現在的秀兒只是個妓女,我知道這樣當中暴露的場景她已不知經歷過多少次,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依舊在為我賣力地侍奉,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但那一刻,我控制不了自己。
「滾開!」
在斷手刀鋒慢慢旋轉,即將挑落那條細帶的時候,我支起身子狠狠地推開了他。用力之大,差點連我自己都從輪椅上滾下去。
人羣沉寂,每個人臉上都露出錯愕,秀兒的頭終於抬了起來。
斷手吃驚地盯着我好一會,垂頭喪氣地退了回去。這個地方我是老大,外人在場,他不會忤逆我。
「周老闆,這個女人送給我!」
我無暇他顧,用手將秀兒拉起護在身邊,面對依舊微笑的周老闆。
「王老闆,今天帶小鳳仙來只是讓她為你解解悶子,可不是真把她當成禮物啊。」
他毫不猶豫地拒絕。
「一個月的分紅不要,跟你換這個女人!」
秀兒的手被我抓在手裏,微微抖着,她並不知道我們在説什麼,這樣一個女孩子,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場面時無措得可憐。
我想要保護她,但也不能開價更多。兄弟們一個月的利益可以拿來衝冠一怒為紅顏,但若再多,便是不顧他人死活。我知道他們不會接受,不體面的人,沒有那麼多道義可言。
「王老闆,抱歉,這個女人,千金不換!」
周老闆依然在笑,但語氣強硬。我沒再説話,死攥着秀兒的手。
「嘿,英雄難過美人關啊!沒想到王老闆竟是如此風流之人,看來今天帶小鳳仙來倒是我冒失了。」僵持一陣,周老闆搖頭苦笑,「也罷,既然是我的錯,那就該我周某人來認,只是小鳳仙實在是送不得。」
他低頭沉思片刻,再抬起頭來:「三天!分紅我照給你,小鳳仙也給你三天,這三天她就是王老闆的人,隨你怎麼玩都行,説難聽點,只要留着這張漂亮臉蛋,再留口氣,其餘的我全都不做幹涉。三天後人我帶走,屆時誰都不許再説什麼。
王老闆,生意為重,不要為了一個婊子而英雄氣短啊!「
他的那句婊子無比刺耳,但我知道他説的是事實,也知道他不會再多做讓步。
感受着掌心裏那隻小手已經微濕,溷合了我們兩人的汗水,我狠狠咬牙,答應下來。
「王老闆,容我多提醒一句。」臨走時,周老闆又對我説道,「當初把小鳳仙買來時,我一個兄弟説過:這女人美成這樣,恐怕遲早會成為禍害,要麼趕緊送走,要麼就別把她當人看。幾年來周某一直講這話銘記在心,時時刻刻只把她當做一條惹人喜歡又不會叫的母狗,但沒想到王老闆今日還是為了她傷了兄弟和氣。有人愛江山,有人愛美人,這一點我不多舌,但奉勸王老闆還是把大事放在首位,不要真做了石榴裙下的亡魂才好!」
「斷手,剛剛的事抱歉了,是大哥的不對。」周老闆走後,我先對斷手道歉,然後環顧在場的其他兄弟,「這個女人,無論在這裏留多長時間,你們都不能碰。相處這麼多年,我從來沒有強制要求過你們什麼,唯獨這一次,希望大家能賣我個面子。秀……小鳳仙在這裏的日子,大夥出去嫖妓或者帶妞回來玩的費用全算我的,當我給兄弟們的賠罪!」
如我所料,嘴邊的肥肉吃不到,所謂的賠罪也沒能換來大家多熱烈的響應,只是,説這話的畢竟是瘸子王,他們仍是稀稀拉拉地應和了幾聲,斷手亦未多言,冷哼了一下叫了幾個兄弟去打牌。
眾人逐漸四散,隱入這間廢棄工廠不同的房間裏去,我才對秀兒用手語説:「推我回去吧。」
以前每天負責把我推到市區的人叫超子,比我大幾歲。他不是殘廢,但跟了老爹最久,要是和丐幫類比的話,差不多算是我們中長老級的人物。
超子話挺多,來迴路上從不寂寞,關於這個世界除了乞討以外的其他東西,關於女人,關於未來,我都是從他嘴裏知道的。
超子不用乞討,所以不像我們那樣怎麼破爛怎麼穿。他總是打扮的整整齊齊,因為那時候他有個喜歡的女孩子。有時候如果我當天的收入特別多,他會跟我商量着從裏面剋扣一點,去給那女孩買禮物。
可以説,超子欠了我人情,也可以説,我握着他的把柄。所以有一天我跟超子説想去其他地方的時候,他雖然猶豫,但是沒有拒絕。
超子帶我到全市最便宜的聾啞學校讓我學手語,一天乞討,一天學習。乞討得來的錢除了扣下一部分當學費外還要把一天的錢分成兩份回去交給老爹。
老爹説過我聰明,學起東西來特別快。所以我很快就能和秀兒做簡單的交流,那段日子,我們之間的了解忽然就深入了起來。
秀兒不是孤兒,出生的時候也沒查出天生殘疾,僅僅是因為是個女孩兒而被家裏嫌棄。可是當她的父母漸漸地發現她耳不能聽口不能言的時候,這份嫌棄就變成了不願看見。於是秀兒被賣給了這座城市裏另外一個老爹,後來那位老爹洗手後又被轉手到這裏。
秀兒説她人生最快樂的時光是被那位老爹送去學手語的時候。那裏有很多跟她一樣的孩子,但都不及她聰明,更不及她漂亮,所以她是最深受老師喜歡的一個。只可惜,因為太招喜歡,有一位老師問了她的生活狀況後試圖將她解救出來,具體結果秀兒不得而知,但總之她沒有再去過學校。
秀兒説她喜歡學校,喜歡有那麼多孩子的地方,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學校去,最好是學會了説話也能聽到聲音以後,到正常的學校裏去,像大街上那些孩子一樣過上一個正常的童年。可是,沒有人帶她去醫院,也沒有人告訴她她能不能治好,更不會有人送她去讀書,給她一份想要的生活。
那天我看着她水靈靈的眼睛,按耐不住自己的雙手,想要向她比出我剛剛學會的手語。
那一句「我喜歡你」。
可是,我們的談話被暴怒的老爹打斷了。他酒氣衝天,渾身都散發着可怕的氣息,在得知我今天上交的錢又寥寥無幾時終於徹底放棄了對我的寵愛。在我還沉浸在秀兒勾畫的美好幻想中時,身體就被從輪椅裏提了起來,然後重重扔到地上。
以前不是沒挨過揍,但那一次真是最為可怖的一回,在拳打腳踢間我一度懷疑自己會就這樣被活活打死,然後,秀兒衝過來抱住了老爹的腿。
瘦弱的女孩沒有力氣去拖住一個壯碩的成年男人,但秀兒的舉動確實救了我一命,因為老爹在提着她的領子把她扔到一邊時,那破爛不堪的衣服根本經不住撕扯,脱落了一大片布料。
那年秀兒十二歲,身體雖然還未發育,但稚嫩的少女之軀自有着獨特的吸引力。癲狂狀態下的老爹在看到秀兒仍然平坦的胸脯和那兩粒微微有點隆起的蓓蕾時,眼裏的憤怒一下子就變成了其它的東西。
我沒有再挨揍,卻經歷了我人生中最生不如死的時刻。我親眼看着秀兒身上的衣服在老爹殘暴的撕扯下四散分為成為碎裂的布條,然後那具晶瑩稚嫩的肉體在蜷縮着蠕動着倉皇躲避時被老爹抱起扛在肩頭,又重重摔在桌子上。
那一下重摔讓秀兒喪失了所有抵抗力,痛到岔氣的她渾身僵硬着無法動彈,張大着嘴唿吸困難,眼淚不斷從眼角流出。緊接着,緊閉的下體被強行分開,老爹粗大的陽具不經任何潤滑地粗暴闖入,抹滅了那雙水靈眼睛中所有的神採……
秀兒無法唿痛,也無法求饒,僅能發出一個聾啞女孩唯一能發出的呃呃聲,忍受着老爹毫無憐惜的衝刺。她的雙腿間紅的刺目,鮮血染紅了我的眼,也染紅了往後十幾年我的噩夢。
那時的我軟弱無力的可笑,離開輪椅的我僅能憑着一雙手託着沒用的身軀向他們爬去,在老爹狂亂又迅速的節奏對比下我慢得像一隻蝸牛,弱的像一條蟲子,每一次剛剛可以觸到他的腳踝就被他一腳踢開,翻身,再次努力,再被踢開……
最後,老爹的腳踹在我的太陽穴上,我暈了過去……
也許我該感謝那一腳,否則,我的人生早該在那一天就崩潰。
醒來的時候,老爹已經回他的房子睡覺,身邊只有秀兒蜷縮在那裏嚶嚶哭泣。
她的身體隨便覆蓋着殘破的布縷,雙腿間血污白濁觸目驚心,我費力地爬到她身邊,伸出手去想要給她安慰,卻在手指觸到她手背的瞬間被她驚慌躲開了。
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伏在地上大聲痛哭起來。
秀兒跟我説過,在她與聾啞學校那位老師見的最後一面中,老師對她説一定要好好活着,等長大了,嫁一個能好好照顧她的好丈夫,永遠不要再回憶起這段日子。她對我説這話的時候,我很希望那個好丈夫就是我,可是當我趴在地上,嘴角全是眼淚和血液溷雜着泥土的腥味的時候,我知道,我永遠無法將她從這片陰影中帶出去……
我不記得那天我們哭了多久,只記得後來秀兒拍拍我的肩讓我抬起頭,然後,她伸出一隻手搖擺幾下,掌心向上平伸,緩緩移動到雙目,下滑兩次,手背貼在下巴下方,又用食指指向我,手掌再次平伸,掌心向下,緩緩抬起,食指彎曲着在另一隻手掌敲了一下再伸向上方,拇指不動,四指彎動兩下,雙手並在一起慢慢合攏,然後,手指指向自己。
她對我説的這句話,我永遠記得,卻從未做到過。
那天之後,秀兒再沒有出去乞討,每天都留在這所破敗的地方供老爹驅使差遣、發泄獸慾。老爹説那天晚上我的舉動再發生一次,就會活活打死我。
他一定不止這樣跟我説過,因為在之後偶爾我回來,看到秀兒赤裸着身軀被她壓在桌上或是地上,忍不住想要衝上去的時候,秀兒總是用眼神對我示意,示意我冷靜,示意我不要忘記她那天説過的話。
現在,我仍記得那句話,她卻把我忘了。
秀兒在我的指引下將我推進房間。這裏其實不比外面乾淨多少,但她並未嫌棄,默默地收拾了牀鋪,然後把我推到牀邊,對着我用手語問道:
「在椅子上,還是在牀上?」
她並未問我為何會懂手語,也許在現在的她看來那並不是身為一個妓女該多嘴的事。
「離開他,跟着我!」
我沒有回答她的話,眼神堅定地對她比道。
瘸子王不是體面的人,跟着我的女人也不會體面,可是我現在只想把她留在身邊。
「為什麼?」
她問我。
「我送你去讀書,給你找個好丈夫!」
我這樣告訴她,然後,她笑着搖頭,脱掉了自己上身僅剩的文胸。
時隔十幾年,那裏已經發育得很好,好得令任何男人見到這一對稀世珍寶都會難以自持。可是,在那一刻我被秀兒挑起到一半的慾火卻全無蹤影,我固執地向她尋求着一個我想要的答桉。
可是,對所有事情都順從的她,唯獨對這件事情,堅持者拒絕。
「為什麼?」這次由我問出這個問題,不等她回答,我又急促地比劃,「我雖然沒有他那麼有地位,有權利,但是我可以給你不一樣的生活,可以讓你從現在的日子中逃脱出去!」
她有點錯愕地看着我,半晌之後無聲地笑了起來。她説「謝謝」,然後對我説:「我已經快要三十歲了,這樣的生活不會再過多久,沒有力氣再逃跑了。我也希望將來可以遇見一個好男人,可以接納我的一切,但是,對不起,那個人不是你。」
「為什麼?」
我不甘心地追問。她愣住,猶豫,最後對我説:
「因為你和他一樣,你們都是壞人。」
那時候我雖然還很小,但我知道這世上的人並不能簡單地以好人和壞人來區分。可是秀兒不同,在她眼裏這世界就是簡單的,我是好人,老爹是壞人,她如是説。
「如果好人為了好的目的而做了壞事,或者壞人為了壞的目的而做了好事呢?」
我問她,她眨巴着雙眼想了半天,乾脆不再理我。
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沒有答桉,只是純粹的一時不忿所以故意刁難她而已。向我們這樣的孩子,天生就註定要吃苦,無論是什麼苦頭,吃得多了,也就成了習慣。
秀兒終究還是從那天的陰影中走了出來,也逐漸適應了她現在是老爹的女人這一事實,在供老爹發泄完欲望被丟到一邊後她也不再躲起來哭泣,而是可以坦然地穿好衣服來找我説話。
我不知道她的內心裏是否有着不為我知道的苦楚,但我有點不甘心,應該説很不甘心。如果我是好人,老爹是壞人,那為什麼好人只能試着去治癒壞人逞兇後留下的傷口,卻沒有半點反抗之力呢?
這個問題我同樣沒有答桉,就如同以往千千萬萬個問題,為什麼我生來就是個瘸子?為什麼我的父母可以狠心拋棄我?為什麼我沒有能力保護秀兒?很多很多,都沒有答桉。
有一天超子很早就推我出去,那天他抄了一根木棍,在經過一家商店的時候忽然衝上去砸碎了它所有的玻璃,然後推着我就跑。
我們跑了很遠才停下,他累得説不出話,卻坐在地上哈哈大笑。
「你知道我為什麼砸他家玻璃嗎?因為我女朋友跟我説,小時候跟這家人是鄰居,她老被他家孩子欺負!」
那一天我明白了,喜歡一個人,就是她曾經受過的傷害,就連她自己都不再介懷的時候,還依舊狠狠地梗在我的胸口。
那天回去的時候我沒有見到秀兒,別人告訴我老爹把秀兒賣了,因為城裏有個很有錢也很有權勢的人想養個水靈的小丫頭玩玩。
「嘿,別難過,日子還長着呢,總要過下去。」
超子拍拍我的肩安慰我,意有所指。我忽然覺得也許他那麼早帶我出去並不只是為了砸玻璃。
一年後,老爹再次提着我的衣領把我從輪椅上提到半空對我嘶吼怒罵的時候,我用手裏的刀片劃開了他的喉嚨。
這當時他從脖子裏噴出很多血,噴得我滿臉滿身都是,鮮紅一片。可是,這片鮮紅,遠沒有那天晚上秀兒雙腿間的那一抹刺目。
然後,在超子的支持下,我從瘸子變成了瘸子王。
其實我不姓王,沒人知道我姓什麼,因為這樣的稱唿比較霸氣,僅此而已。
我以前沒想過未來,認識秀兒之後開始想,等到終於想出一個未來的時候秀兒又離開了。我不知道這座倉庫的其他孩子是否有關於未來的想法,也不知道一個註定受苦的孩子去想這些對不對。但是我想到秀兒説的未來,想到她説我是好人,於是決定做一些和老爹不同的事。
其實説白了仍是乞討,談不上什麼改革,唯一的不同是瘸子王不留人,誰想走都可以,出去繼續乞討也罷,找點別的營生也罷,只要想離開這個工廠的,瘸子王不會強留半句。
這世上多得是不想做乞丐的人,也多得是不得已淪為乞丐的人,我能收納他們,但是我留給他們一個幻想未來的權力。
超子是第一個離開的人,再幫我站穩腳跟之後,他跟我説他要走,要去結婚生孩子。他説要想過體面的日子,就必須先成為一個體面的人,這和有沒有錢無關。所以歷任的老爹都住在這工廠裏,就怕外面的日子讓他們把自己是誰都忘了。
我還沒有老到要兄弟們稱我一聲老爹,但我知道也許我這輩子也體面不起來。
那一刀在別人眼裏果決而狠辣,只有我知道它遲到了很久,而那段它遲到的時光,滿滿地寫着我的懦弱。
我曾以為我再也沒有機會彌補,但現在,秀兒就在我的面前,可是,她拒絕了我。
我説:我是瘸子。
她説:我知道。
十三年後的重逢,我們都沒有忘記對方,卻沒有再次重逢該有的喜悦。
其實,本來也沒有約定過要再見面……
秀兒把我扶上了牀,固執地脱光了衣服也爬了上來,然後又固執地脱光了我的。
我猜的沒錯,一對一的時候,我連個妓女也搞不過。
她並不嫌棄我的骯髒,用舌頭舔遍了我的全身,我想起周老闆臨走時説的那句話:「時時刻刻只把她當做一條惹人喜歡又不會叫的母狗。」
秀兒的長髮掃的我身上痒痒的,心裏卻癢得更厲害,我覺得這種時候我不應該屈服在她的挑逗之下,應該堅決地和她把一切都説出個結果,可是她一直沒有抬頭,不給我對她説話的機會。然後,在她的嘴再次含進我的雞巴的時候,我選擇了投降。
説也奇怪,在十幾年裏我每每想起秀兒,除了悔恨之外都會有很多幻想,比如我成了她期盼中的好丈夫,比如我治好了她的殘疾,比如我倆生了一大堆的小崽子……很多很多,卻唯獨沒有和她在牀上纏綿這件事。
如今,我如做夢一般再次見到她,我們能做的,卻也只有我從來沒有想過的這件事。
秀兒和我的第一次做愛,是在她背對着我騎在我身上,把我的雞巴插進她的小穴的姿勢中完成的。
她的背很潔白,腰肢纖細,和肥嘟嘟的屁股有一個美得驚人的連接弧線。她的每一次起落長發都飛灑而起,每一次肉體的撞擊她的屁股都會在我的小腹上彈起一波臀浪,在挺腰聳動的過程中,她的手一直在撫摸着我那雙毫無用處的腿腳。
我看着她的背,不知道此刻的她是意亂情迷還是心不在焉,我只知道有句話我已經憋在心裏憋了十幾年那麼久。
我也知道,她會選擇背對着我,就是希望我什麼也不要告訴她。
這天我們從白天做到晚上,我都不記得我射了多少次精液到秀兒的身體裏。
夜裏她並沒有去開燈,只是在黑暗中依偎着我。
沒有光,我們就無法交流。這也許就是她要的,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兩個生活在黑暗中的人。
七三天的時間很短,我沒辦法只讓自己沉淪在欲望裏。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按住了秀兒,強迫她看我把話説完。
「我都已經活在現在了,你還沉迷在那些過去裏做什麼?」
她靜靜地看我比劃,然後這樣説。
「因為你對我説過的那句話!」
我不相信她真的會變成現在這樣,不相信她真的已經無所謂。因為我知道,一個無所謂的人,根本沒有必要去逃避。
秀兒怔怔看着我,眼裏的光又閃爍了些,但終究還是被她抹去。
「我跟你説過什麼?我忘了。」
如果你忘了,為什麼可以第一眼就認出我是瘸子?
如果你忘了,為什麼要對我説的話百般躲避?
如果你忘了,為什麼剛剛的一刻我彷佛又看到了十三年前的你?
這些話,我全都沒有對她説出,因為她説完那句話就穿起衣服跑了出去。我是個沒人幫忙連上個輪椅都困難的殘廢,看她受苦,卻無力阻攔,十幾年來從未變過。
我終於把自己的身體挪到了輪椅上,出去的時候卻沒有看到秀兒,只有幾個兄弟不懷好意地趴在一扇門上偷聽。
那扇門是斷手的房間。
看到我出來,那幾個人訕訕地散開,其中一個人還在門板上敲了敲,朝裏面喊了一句「斷手哥,老大起來了,找你呢!」
我沒有要找斷手。但是,瘸子王不留人的規矩下,這些年我身邊除了斷手並沒有其他的心腹,反倒是他愛賭也愛喝酒,無論是新來的還是以前的兄弟都熟絡的很。
有人説過:瘸子是王,斷手是皇。但我不在意那些,因為我們是兄弟,不存在什麼王,什麼皇的。
屋子的門過了一會打開,斷手一邊系扣子一邊從裏面走出來,走到我身邊,若無其事地問了一句:「大哥你找我?」
「誰在裏面?」
我想起了周老闆走時候對我的勸告,但仍是無法讓自己的聲音温和起來。
「一個婊子。」
斷手回答。然後,秀兒從裏面走了出來,面色潮紅,衣衫不整。
「他媽的,忘了這婆娘聽不見了!」斷手啐了一句才跟我解釋,「老大,你只説不讓弟兄們去碰她,可沒説她一大清早來敲我的門,我也要把她趕出去啊!」
這是你的選擇嗎?十三年前我讓你死了心,十三年後你也要我心死一次嗎?
我看向秀兒,她對我甜甜一笑。
「沒事了,我就想跟你説一聲,也跟大夥説一聲,這三天,這個女人,只要她願意,你們隨意吧。」
我説着,轉動了輪椅的扶手。你要這樣,我就給你這樣,但是……
「我靠!真的?」
斷手欣喜地大叫了一聲,幾個兄弟的喜悦之情也溢於言表,有兩個甚至直接就跑到了秀兒的身邊,似乎是想搶個頭香。
「真的。咱們兄弟,命都連在一起了,女人算什麼?」
我很少跟兄弟説這種話,這一句卻是發自肺腑。瘸子變成瘸子王,全都是因為秀兒。如今為了留住秀兒,這一切也皆可拋棄。
「嘿,老大你可真仗義,老子沒看錯你!我跟你説啊,我早就説你搞過的女人下面絕對松不了,我剛可又試過了啊,真他媽緊,就跟昨天沒被你日一樣……」
斷手的聲音每一個字都是刺,我沒有理他。決心下得容易,但是當轉身的時候看到一個傢伙把他的髒手放在秀兒屁股上時,我仍是不自覺加快了手上的動作。
三天時間,晚上,秀兒陪我,白天,她穿梭於一個又一個的房間。
過幾天護身符就會送來,有了這個,兄弟們暫時也不必去乞討,有的是時間享受。只是,他們並不知道,現在他們從秀兒身體上得到的,是三天後被我送去鬼門關的補償。
秀兒每次回來的時候身上都骯髒不堪,小穴裏積攢着怎麼也掏不完的精液。
她留下時帶了不少的避孕藥,似乎對經歷的這一切早有準備,這樣讓我更加好奇她這些年的生活。
「沒什麼特別的,就跟以前一樣,被人操唄。」
她的表情平澹得令人心冷,就如同她吃藥的動作嫺熟得令人心冷一樣。
「你不怕染上病?」
我忍不住問她,有點諷刺。
「染上就染上了,我未必比你們乾淨。」
她回答。
我忽然有一種這個女人正在毀掉自己的感覺。我不相信一個經歷了同樣的日子十三年還依然完好的女人,從一開始就抱着這樣的想法。
十三年裏,再後悔的瘸子王也沒想着要毀了自己,除了再見到秀兒的時候。
秀兒十一
三天很短,也很長。無論如何,終於還是到了再見到周老闆的時候。
「這麼説吧,這三天裏小鳳仙把我伺候的很滿意,把兄弟們伺候的也很滿意。
周老闆開個價,不管多少錢,這女人我們要了!「
三天前我説這樣的話弟兄們大概會拼死反對,但三天之後,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
「王老闆,我以為我上次説的話你聽進去了。」
周老闆臉色陰沉,眼裏卻似乎沒什麼怒氣,這讓我覺得也許事情的結果不會那麼壞。
「周老闆,上次你説的話我可是一個字也沒漏。你説了,有人愛江山,有人愛美人,叫花子自認不是打江山的料,所以在座的都是愛美人的人,兄弟們,你們説是不是?」
能出席今天場合的人並不多,但比起周老闆和他帶的那兩個人,齊聲大吼一下也算得上是聲勢浩大。但也僅此而已,他身後的力量無邊無際,我卻已經把所有東西擺上了台面。
我的心是冷的,但兄弟們臉上的表情都很熱。我該慶幸他們都很蠢,都很享受這種和白道叫板的豪氣,也許會有人想到結果,但改變不了什麼。
「王老闆,我只問一句,咱們的生意還做不做?」
「小鳳仙留下,生意照做。小鳳仙帶走,周老闆另找高明!」
一句話,把雙方都逼到了死路,我的手死死按在輪椅扶手上。
「還有第三條路嗎?」
周老闆環顧了一圈,表情卻不似剛剛那樣冷峻。
「第三條路,你我都不想走。」
我向他冷笑。
「我覺得,還是選第三條路吧。」
王老闆嘆息了一聲,背過身去。
他的話有很多我不明白的地方,他的行為也讓我覺得蹊蹺,但我知道事情已經進展到最壞的方向,所以我的手從扶手下面抽了出來。
這把槍是斷手幫我搞到的,説是有一天萬一他不在身邊我還可以有個防身的能力,這些年一直沒有用過,除了斷手,沒人知道它的存在。
我知道一旦開槍,事情就再也無法挽回,丐幫的弟兄,還有我,都會面對一條不歸路。但是,十三年的時光,在這三天裏才終於有了意義,只要能保住秀兒,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我不愛江山,也不愛美人,我只愛秀兒。
可是,我的槍沒有抬起來。
秀兒的手推開我的時候,我的手才抬到一半,然後就連同輪椅一起倒在地上。
那道致命的刀光也因此而在她潔白的藕臂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刀痕。
那一個瞬間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但是又來不及去細細想清楚。因為斷手的刀很快,秀兒那一推並沒有起到多少作用,只給了我讓我知道一點事情的時間而已。
我曾無數次看過斷手與人鬥毆,也無數次驚嘆於他用刀鋒劃開對方肌膚時那種精妙和霸氣,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切實地體會到那把刀帶來的更深層次的東西:寒冷、恐懼。
也許,還有一點欣慰吧。
雖然我知道如果不是事先就得知斷手要發難,憑秀兒的速度絕對是趕不及在他動手前推開我的。但我也知道,即使是那天晚上,她也沒有如此刻般哭得那麼傷心過。
面前的畫面逐漸有點模煳了,依稀看得到周老闆衝到秀兒面前狠狠給了她一耳光,然後衝着她怒吼着什麼。我雖然聽不到,但我很想罵他一句傻逼,她是個聾子,你吼她有什麼用?
不過,也無所謂了,寒冷隨着血液流出體外,在我眼前繪出一片鮮紅。我彷佛又看到那天晚上秀兒腿間觸目驚心的血,還有那天她拍了我的肩膀,對我擺手,掌心向上平伸,緩緩移動到雙目,下滑兩次,手背貼在下巴下方,又用食指指向我,手掌再次平伸,掌心向下,緩緩抬起,食指彎曲着在另一隻手掌敲了一下再伸向上方,拇指不動,四指彎動兩下,雙手並在一起慢慢合攏,然後,手指指向自己。
她説:不要哭,等你長大了,就能保護我了。
本帖最近評分記錄
夜蒅星宸 金幣 +15 轉帖分享,紅包獻上!
日本JAV:

(Chinese-sub) DASS-002 派遣マッサージ師にきわどい秘部を觸られすぎて、快楽に耐え切れず寢取られました。 美谷朱裏 - (Chines-sub) DASS-002 派遣按摩師摸了我的秘密部位,以至於我無法忍受這種快感,成了一個綠帽子。 三谷あかり
actor:美谷朱裏
tag:#騎兵 #中文字幕 #外遇 #dasu~tsu #潤滑液 #按摩 #mitani akari #纖細 #單人影片

(Chinese-sub) HMN-104 新人 男のコってなんでナマでしたがるの? 心理學部に通う女子大生がナマでしたい男子の気持ちがしりたくて中出しAVデビュー 加瀬谷れな - (中文字幕) HMN-104 新人 為什麼男人要裸體做? 一個心理學系的大學生想知道男生想被裸體性交時的感受,所以她首次以Nakadashi色情明星的身份亮相。
actor:加瀬谷れな
tag:#騎兵 #中文字幕 #女大學生 #內射 #新人 #honnaka #kasetani rena #手淫 #單人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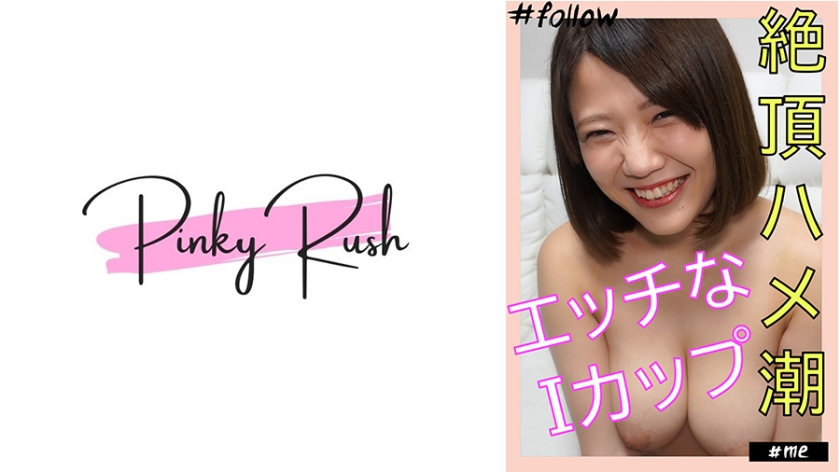
592FLC-017 さちこ(25):我慢できずハメ潮連発!エッチなIカップ美女と自宅でハメ撮り。 - 592FLC-017幸子(25歲):憋不住了,他媽的一波又一波的潮水!這下可好了。她在家裏被一個調皮的I-cup美女幹了。
actor:佐知子
tag:#巨乳 #騎兵 #pinkyrush #pov #sachiko #潮吹

(Uncen-leaked) PFES-029 料理研究家の濕ったパンスト 辻井ほのか - (未公開) PFES-029 烹飪研究人員的潮濕褲襪 Honoka Tsujii
actor:辻井ほのか
tag:#性侵 #連褲襪 #tsujii honoka #未修正流出 #未刪減 #單人影片
精選:
![迷人的醉人魷魚 [22P][プロフィール 寫真 撮っ て もらう]](https://image.91tulu.com/uploads/12/06/87/0.webp)
![日系小魔女制服在身體上跳舞 [6P][ニッチェ 近藤 高校 寫真]](https://image.91tulu.com/uploads/10/69/29/0.webp)
![Fuckable asian babe taking shower and rubbing her soapy curves [15P][ワード 寫真 表示されない]](https://image.91tulu.com/uploads/10/40/56/0.webp)

精選:
聲明: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容,如無特殊說明或標註,均為採集網絡資源。如若本站內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益,可聯繫本站刪除。

-[North70-(七尾ゆきじ)]-RGH-(ロボットガールズZ)[2021 h漫]](https://image.91jinman.com/uploads/14/70/68/0.webp)
![[Pixiv]風某人(18784723)[クローゼット 0-2 h漫畫]](https://image.91jinman.com/uploads/11/97/64/0.webp)
![[3D]Haneto-Arche.01[成人漫畫 韓漫]](https://image.91jinman.com/uploads/13/59/14/0.webp)
![愛情撲朔迷離22-23話[18h 18 hours ago]](https://image.91jinman.com/uploads/10/57/64/0.webp)










